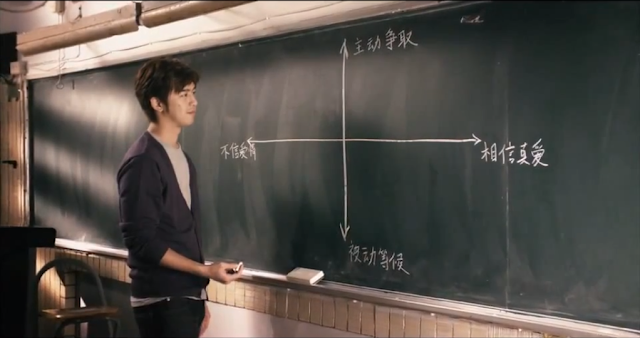爲何非寫不可,非理論不可?——(題記)
我將小王子的日記塞進枕頭,闔眼沒四小時,手機鬧鈴已經嘰喳作響。
睡醒後幾乎把隨身背包塞滿,帶上自己厚重的筆盒出發。和班長原定的會合地點轉移到甲洞車站,售票櫃檯處湊巧遇上準備前往同一地點的伍燕翎老師。我說怎麼老師的樣子看起來好眼熟,當她轉過身,即刻被我們認了出來。
燕翎老師是待會的主持研討會的開場司儀,她開著玩笑告訴我們要是跟著她就不怕遲到。等待列車抵達前半小時,班長和我向老師略述各自近況,她談她一年來外文系熬過的日子,我則提起前幾天電郵里的入學通知。
七點四十分,遲到的列車才徐徐停在月臺。
上車之後,班長和我在車廂銜接的通道處找了個站位倚著,通道內壁因列車高速移動產生摩擦,發出咿呀咿呀的聲響。班長說這跟臺鐵相比之下遜色得多,誒,看這列車蠕動得還挺劇烈呢。
列車離開吉隆坡中央站才空出了好些座位,耗費將近二十分鐘的時間,列車終於駛入加影站。兩人於是緊跟著燕翎老師的腳步走出車廂,經過檢票員站崗的地方,值班的正是去年八月對我和紅傘一夥人開罵的檢票員,身形依舊略胖,但站在人海茫茫的關口處,見盡無數旅者遠行的足跡,恐怕也不記得眼前這位遞票給他的列車乘客吧。
能記住檢票員這個過客,究竟是我念舊,還是我記仇?呵呵。
車站外又是站成一團的德士司機,他們忙走上前,口中叫著【Taxi?Taxi?】地詢問剛下車的乘客是否需要載送。我擺出禮貌的微笑婉拒,尾隨前面班長的腳步跟上去。

越來越接近學院的人行道上,我的手機接到一則信息。
【你們倆在搞什麽鬼?】墨契藍在信息後面多加一對白眼的表情符號,嘿這女孩老是不能把她擱下,否則她可會悶壞的,那妳去北大以後咋辦啊小姑娘?
四樓的講堂門外,報到處滿滿擺著一沓沓的影印筆記和黃色卡紙文件夾,負責報到的工委替我們分發組別。會場外墨契藍從一角冒出,淘氣笑著向我們打聲招呼。咩揚從右邊走來,右手輕輕點了班長的右肩,然後出現在她的左邊。
眾人相互問安后相繼依照組別做好在座位上,大家選了大抵鄰近的座位(方便討論),實際上當過學生的我們,自然而然想在課堂感到某個鬱悶的時刻,至少找到一個對象替自己的無聊解圍。
仔細查過分組名單,才知道作家半老大也參與其盛同夫人來研討會報名。來自南部的圣祥兄早在我隔壁的隔壁端坐,身上裝扮並無多大改變,深色系的上衣和外套,配一頂低調的鴨舌帽是他的風格。近來他在南院的名聲不俗,也因自己的投入學習的熱忱,談笑間總露出開朗笑容夾雜丁點傻氣的他,就讀中文系第一年已經引起關注。現在還多了個【缺愛副主席】的名堂(典故不明,有待查證。)
理論研習第一天由黃錦樹以及賀淑芳兩位老師主持,錦樹老師大概讓學員瞭解何謂文學理論,逐步進入各式各樣的書寫風格。從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,聊著聊著互文性再回歸馬華文學為何需要理論的課題。裏面有我所摸不著頭腦的恩仇,馬華文學斷奶輪大致聽懂了,然後錦忠老師不時挑起的【焼芭事件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則不得而知。
面對這般極需學術技能的場合,平日投身于創作的九字輩們難免感到措手不及,甚至連中文系的圣祥兄和讀過一些文學概論的班長也顯得有些吃力。墨契藍在我跟前搖搖頭,我盯著筆記內文看,皆是我一知半解的文學評論,也唯有跟著講座的速度窮追不捨地思考。
當理論碰上創作,起初的摩擦是劇烈的,甚至互相剋制。筆者之所以書寫,全賴作者一股想要表達的由衷,因此創作的【根本】很重要,所以筆者也就不會拘泥于任何形式的書寫,專心致志的在呈現自己的想法,偶有動用一些寫作上的技巧,讓作品生色。
然而經歷一段可觀的書寫以後,當作者的文本將被評論家解析,并賦予作者一個形式上的冠冕。換個角度想,舉凡藝術的事都很主觀,每個人會用他們特有的審美方式切入文本,結果得到的感受也不盡相同。
林建國先生和錦樹老師在文學觀念的分歧,很顯然的,他們已經走向各自的【文道】。
文學理論上無可厚非的是,任何情況下的理論總會有其限制,並不會出現能夠縱觀一部文本的完美公式。有異于科學理論,它具有極大彈性,既不能全然被推翻,也無法確切的鞏固。彷如物理學上“ 光的波粒二象性 ” 所言,單一理論不能讓光的本質有絕對的定義,也因此光被解釋成具有兩種不同的性質。
理論需要各種聲音作為支撐。
 |
| 遭人【圍剿】的龍哥。 |
午休時間同大夥用過午餐,回到會場外的走廊,看見有人出版社的書攤。
擺在桌上的有人系列里有一些從市面上消失了蹤影的早期書籍,身邊經過一個準備付款買書的人,一疊書中正夾著一本《無巧不成書》,反看桌上賣的除了《簡寫》和《因時光無序》,那一本已經售完。翻著書當兒,眼前放了個折扣詳情的牌子,顯眼的寫著令人心動不已的【五本或以上折扣三十五巴仙】字眼。
正在台灣求學哈曼雖然學業上忙忙碌碌,卻也不忘閱讀,更不忘瀏覽博客來訂書。
【博客來買書很簡單,不過是把你要的書點擊,區區幾個鍵就完事。同時,錢也跟著從皮包出賬。】他說得輕鬆,可口袋裡似乎也留下不多盤川了。
假期間兼職書店員工的墨契藍,說到買書也不是什麽省油的燈。前幾天剛從北京帶回十幾本血拼回來的書籍雜誌,現在不也毫不猶豫地忙著挑選桌上的文集。而我也料到龍哥會帶著出版社的書本踩場,老早從積蓄中的流動資金抽出兩張五十塊鈔票待命,一個人就買下了五本書:那天晴的小說《孤島少年的盛夏紀事》、方路微型小說《輓歌》、溫祥英的《清教徒》、禤素萊有關從軍的散文集《隨軍翻譯》和周若濤的詩集《神秘之歌》。
盛惠七十一令吉,書攤的工作人員在收據上簽名。
首日研討會在賀淑芳老師的問答環節告一段落,直至小組的討論時間,全程依然不見半老大的蹤影。
大會結束后,墨契藍貌似約了書店的同事餞別,提早回了家。走廊上僅剩下我、班長、和咩揚,另外有兩個是比我們大幾年的研究生學長姐,其餘的都是文壇裡頭,以錦樹、錦忠老師為首的前輩們。據說前輩們想要找個地方續攤,而走廊上三個後輩略微尷尬的站在一個角落不知去留與否。茫然隨著前輩們的腳步來到大樓底層,最終決定由遲些抵達聚會地點的黃俊麟先生(大家都叫他老黃,是為星洲文藝春秋主編)負責載送我們三個。
約莫十五分鐘,老黃把我們送抵 “ 衛記辣湯之家 ”。這一間家庭式的店面里,招牌顧名思義做的都是些辣味菜色,是由龍哥所介紹的客家菜,于加影一帶馳名。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席一場難得的作家飯局,或許要面對諸位在文壇內打滾且身經百戰的前輩,心情竟莫名的忐忑起來。
邊吃著桌上那些刺激味蕾的菜,我七零八落的聽前輩們提起文壇的三兩事,時而聽懂時而不懂的,說報館里又要有什麽人事更動了,那個誰又要得文學獎了,問班長轉系還是不轉,問龍哥何時跟龍嫂拉埋天窗。
正所謂吃飽喝醉,我們僅是達成前者。老黃此刻從桌下拿起一隻青色的酒瓶,托店員拿來開瓶器,拔出木塞,將紅酒倒給桌上的人。班長和咩揚搖手婉拒,只有我不知死活的要了一點。喝著喝著把杯子喝空后,酒瓶裡還剩一些,錦忠老師問道誰還要添一些酒。不知哪來的膽子,我又要求再來一些酒。
【得了吧,年紀輕輕就別讓他喝那麼多,對身體不好。】溫綺雯老師一副擔心的樣子看著我。
“ 你會品酒嗎?能說出這是哪一年的酒? ” 錦忠老師開始問。
(品酒老實說我不會,但是我剛才不小心瞄到2008這個數字……)
聽見我的回答,錦忠老師爽朗地笑笑,發現了我的作弊行為。
【看,你臉色開始發青了……】溫綺雯老師繼續盯著我看,而我也默認自己已經開始微醺,全身放鬆的感覺真好。

離開餐館臨上車前,咩揚致電阿咲約好時間待會再出來喝一杯,腕錶時間顯示九點半。勞煩龍哥送我們三個一趟,車子停下的時候,夜色正悄悄哄人群散去的車站入睡,末班車開進月臺以前,三人接續未完的話題談創作,講一講花蹤還有之前臥龍幫成員李天才家中多得嚇人的藏書。
咩揚在班長提醒下,驚覺原來自己還有一年時間參加新秀組,士氣振奮些許,終於又提起動筆的幹勁。消息靈通的班長指出,李天才即將席捲不久后頒發的獎項,搞得臥龍幫裡未能投稿者憤憤不平,半開玩笑地揚言要入侵家宅燒掉他堆積如山的藏書。
我們選了夜班列車上其中三個空位坐下,斷斷續續在搭話,眼神透出對未來的一切茫然。沿路途徑國大的車站,我想起女王在小白車上告訴我們國大今年華裔學生的低錄取率,想必一年一度的升學冤案又要再次重演。我告訴咩揚說既然念中文系,大可對本地大學面試官的提問嗤之以鼻,如今東華大學的入學通知到手,乾脆放膽去闖一片天吧。
回到咩揚家中把行李安放好,稍微梳洗便再坐上咩揚的車開往阿咲的家。
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樂乎?
其實跟阿咲混得較熟的日子不多(不過一場營會的長度),後來僅僅借由網絡的幫助我們得以保持聯絡,要是遇上空暇時間,也抽空看看她和咩揚的博文。物以稀為貴,篇篇文章都凝聚生活的力度,雖然沒有我這閒人的美國時間把博文更新得勤,質量上依舊是我所能不及意境。
一路上通暢無阻,但是這時能讓我們坐下閒聊的店面都將打烊,找個嘛嘛檔風格的餐館阿咲說太肥,連珠炮似的建議了好幾處也被逐一否決。
【不如我們上廉航機場,從這裡去大概需要二十分鐘車程。】我當場愣了愣,後來才曉得原來阿咲咩揚的同學沒事也常上機場喝喝星巴克。不一會,黑壓壓的柏油路外圍,不遠處亮出些許紅色和橙黃色光點,是飛機跑道。
向星巴克櫃檯點了一杯冰可可卡布奇諾,我們找到某個靠玻璃窗的角落坐下,一句一句砍大山(閒聊),砍遍三山五嶽。班長重提在辣湯之家龍哥遭好幾人催婚的時候,瞪大眼睛滿臉尷尬的狼狽相;再來胡言亂語些有的沒的神秘傳聞,像極一群來自不同雜誌社的記者互爆獨家內幕的茶會。
當然那些話題里,稍微抓到梗的,一知半解的,自己全無概念的,八卦俱全。
【我覺得啊,管他們文學史怎麼寫,我們寫寫馬華文學野史就好,哈哈哈……】那是班長的幽默。
話題矛頭忽地轉回早上的研習營,我們說起其中一些積極發表意見的中國研究生。畢竟在學術研討這樣嚴肅的場合,鼓起勇氣開口人都是研究生等級,而我這種把創作當業餘興趣的營員只有洗耳恭聽的份。
錦樹老師給予的回應大多很堅定,想必他很清楚自身的學術立場(亦可謂有關學術界之權威),對於任何問題都能篤定回答,沒有一絲躊躇。班長說這樣豈不很像神算先生嗎,本地排名數一數二的物理教師,仿佛定律和法則已操控在股掌之間,運用自如。
對此阿咲顯得不以為意,果然學術於她而言純粹是些不置可否的東西,甚至胸懷壯志想過開創屬於後輩的時代,計劃得大膽又豪邁。
【也不是不可以,我們給自己十年的時間衝刺。到時候我們把紅蜻蜓出版社買下(小孩們啊這世界不只是有真善美!),再來是有人還有大將……】聽上去有點狂妄,在座的我們被這麼一激也覺得這項計劃有他的可行性。十年,太多約定的十年,教我何從想像它的偌大。
【看來你也是那種不受束縛的寫手啊。】阿咲轉頭面向我,隨即談自己喜歡的小說作家。
我所知道的阿咲向來喜歡悠哉緩慢的創作模式,她也屢次表明過自己的習慣。我想一個自由的寫字人理應不被任何立場撼動,縱使把自己寫到邊緣也沒關係。我欣賞她的隨心所欲,心無旁騖去守候那些稀疏的靈感,才能醞釀出屬於她最滿意的作品。
雖說來到小說創作的瓶頸,但事後知道阿咲也在網絡上默默關注著我寫過的博文,心中自此多了一股感動和莫大的勇氣。
那天臥龍幫三缺一,缺席的李天才也即將是我的大學學長,恰好阿咲也在吉隆坡附近的私立醫學院就讀,三人以後或許要相依為命呢。幸運的咩揚,能在他就讀的東華大學遇見阿咲的偶像小說家黎紫書。我也借著這一次機會一睹阿咲對她偶像的迷戀,證實了班長所言。
【我告訴你,不准和她說話。】明眼人也知道她的口氣既羡慕又妒忌,哈哈。
凌晨兩點半,入夜的咖啡店反而愈漸熱鬧,坐滿許多客人。
“ 走啦,我們的研討會心得還沒動筆呢。 ”

淩晨三點鐘,我倚著牆邊用雙膝墊上一張書寫紙開始回顧早上所討論的課題。與咩揚苦思該要如何下筆,大學里歷經過地獄式訓練的班長早寫好了三四行,老老實實的把今日身為營員的疑惑和感想統統記錄,緊接著倒頭便睡。
咩揚也沒花多久便也完成了半頁心得,提醒我若是寫完了記得把房裡的燈關掉。
給手機設定七點的鬧鐘,房裡除了被電風扇吹動的紙張外,只有我醒著。可能有卡布奇諾的刺激,我陷入了深層思考,用手上的黑色原子筆在書寫紙上喃喃自語。自覺那是理性與自己文字所構成的分身正在交鋒,歸根究底,是【寫作初衷的化身】揮刀向我,而我又再握劍抵住攻擊。
【你究竟為何而寫……理論的介入令你有所動搖嗎?】省思的眸光霎時點亮,四周響起回音。
朦朦朧朧被鈴聲里健三倉促的腳步聲吵醒,打從凌晨四點算起,才睡不過三小時有餘。打地鋪的班長關掉鬧鈴后卻也疲累不堪復又睡去,咩揚也背對著我睡得正香。輕輕撥開書桌旁的深色布簾,窗外透進一抹冷靜的晨光,根本就是一副引人賴床的美景。
不好意思叫醒他們,我回到床沿,雙手揉臉企圖讓自己清醒一些,然後悄悄走進浴室梳洗,早上八點鐘才喚他們起床。
然後和預期一樣,我們遲到了。
張錦忠老師已經開始他的分享環節,不時還調侃剛進來的班長,令她一時反應不過來。今天的討論課題有關【開端】,錦忠老師反復提出疑問,目的是要引導學員朝向具建設性的方向思考,培養正確的問題意識。接著他又談一些寫作的主義,要在場學員列出有關本地論文和文學批評的例子,皆是我認知以外的範圍。
【黃子元同學……對吧?你都知道答案……填完了?】
“ 沒,我不曉得。 ”
【一題也不寫?】
“ 呵呵,我真的一題也不會…… ” 這樣說真是失禮啊哈。
第二堂的主講溫綺雯老師更具體的為在場學員解釋某些理論,讓大部份缺乏學術理論根基的學員能夠對理論有清楚的認識(應屬全程聽得最舒服也瞭解較為清晰的一堂)。研討重心多是轉到保羅•薩特的【介入文學】還有羅蘭•巴特的【零度寫作】,亦是【介入】與【抽離】的對立。
在綜合會談里,賀淑芳老師道出了許多創作者極度糾結的課題——當創作碰上理論,會否引起書寫的障礙。
一般剛入門的寫手在創作期間並不在意(甚至不懂)文學理論的應用,他們的感官是敏銳的,也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表達的主題,因此多是著手于表達的寫作技巧。賀淑芳老師和黃錦樹老師同時也補充,當評論文學作品好壞的感知能力已達到極限,我們應該開始懂得學習相關理論,並嘗試以理論賞析文章,好讓賞析達到一定的深度。反之,懂得利用理論的寫作者,更是能抓住讀者的胃,讓寫實更逼近真實場景,讓人信以為真。
次日的分組討論少了昨日的僵局,組員們漸漸開口道明各自對文學的審美觀。輔導員也藉此讓偶爾參與創作的幾位學員發表些感想,可能是需要當做學術的參考吧。討論雖不如他組熱絡,但這是能夠理解的。
研討會的最終,在高嘉謙老師簡潔的結語下圓滿落幕,而馬華文學的力爭上游依然持續著。
後記:
馬華文學現在是什麽?馬華文學可以是什麽?馬華文學將會是什麽?這些依舊無解的問題值得我們一再追尋。像《社交網戰》裡的紮克伯格看待自己的面子書一樣,在地文學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還是很高的,解決困境(談何容易?)唯有多創作,累計文本并期盼經典能在某日奇跡般面世了。
記錄這次研討會的行程、所見所聞,我足足沉澱了一星期。
最近需要好些不同的空間給自己喘口氣,轉移心情。
隨意的找一個分身,逃進不同的人際關係網,褪去一個長久持有的外殼,當另一個自己享受短暫的有新意的經歷。
阿管在《五分鐘完事》里說:【其實,很多時候不是別的地方比較好,而是我們厭倦了原來的地方,或許,我們還厭倦了在原來的地方的自己啊。】
那麼如今的我更認識了自己嗎?還是……又找到了另一個陌生的分身?